骓的繁体字怎么写
騅
「书物」2021年12月师友赠书录(九)韦力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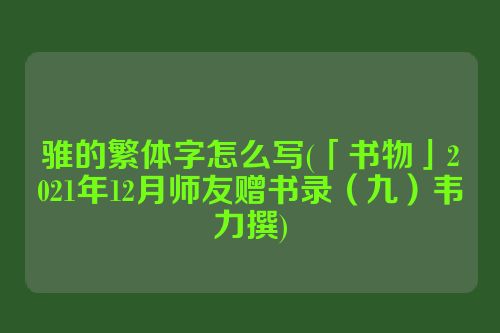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4期,姜小青主编
本期中感兴趣的篇章有吴怀东《尴尬的相遇与遗憾的错过》。
一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作为法官审问过诗圣杜甫,因此彼此的诗文中均不会谈及对方。
唐至德二载四月,杜甫从长安城逃出,投奔唐肃宗凤翔行在,其忠诚令唐肃宗感动,很快任命他为左拾遗。
杜甫被授左拾遗的诰文原件在明末清初时被钱谦益亲见于杜富家,上面写着“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
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故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
没有想到的是,杜甫刚被任命为左拾遗几天,就上疏救房琯,因为房琯组织军队与叛军作战时,简单的生搬兵书,故一败再败,令肃宗震怒,要追究房琯责任。
左拾遗为言官,杜甫认为“zuì细,不宜免大臣”,所言令肃宗十分生气,于是杜甫被下狱,“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搭救,才获免zuì。
当时审理此案的人就是颜真卿。
虽然颜仅长杜甫三岁,但其为官经历要比杜甫长得多。
至德元载十月,颜真卿放弃平原郡,投奔肃宗行在,肃宗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因房琯之案,两人有了尴尬的面对。
那时颜真卿正在dàn劾房琯集团,他的所为间接导致了杜甫政治生命的结束。
历史值得玩味之处,正在于这种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心理吧。
马瑞芳《〈西游记〉也有女主角》也颇有趣,文章谈及大多数人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没有女主角,虽然三国中有貂蝉,水浒中有“四大yín妇”,《西游记》中有层出不穷的女妖,但都是过眼即逝,没有贯穿xìǎo shuō始终,没有一个能影响整部xìǎo shuō的情节 ,也没有一个能与xìǎo shuō男一号息息相关,但是马瑞芳却认为这种论断有些绝对,她觉得《西游记》中也有女主角,那就是观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基本贯穿《西游记》始终,并且是和男一号交往最多的女性。
读到这里时,人们会疑惑于观音菩萨是女的吗?马瑞芳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有所介绍,她谈到观世音在成佛前是转轮圣王无净念的太子,男性,但后来却渐渐变成了女性。
那么,西天取经时的观音菩萨是男性还是女性呢?该文中没有提及。
但作者认为,《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是吴承恩按照“中华民众的愿望,按照明代士子审美需求创造的观音”,所以作者认为,“《西游记》的观音菩萨是女真人、女善人、大美人”。
既然如此,对女妖怪深恶痛绝的孙悟空会不会爱观音菩萨呢?可惜吴承恩没说。
陈尚君的《唐代的谶言》谈到隋末大乱,隋炀帝久困扬州,但他对重要的人事安排并未放弃,他选择李渊任太原留守,因为李渊的母亲与炀帝之母为亲姐妹,想来这层关系也是信任的基础。
当时太原是与突厥对抗的前线,故李渊拥有重兵。
隋炀帝把亲信安排于此,可惜看走了眼,李渊到任立即袭shā隋帝的亲信,随即以勤王之名夺取关中。
当时群雄并举,李渊初时不具备一统天下的实力,于是先立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
转年炀帝被shā,李渊称帝,他在加强军备的同时,舆论宣传也立即跟上,大造童谣,谶言风靡一时。
贞观年间,流传着“当有女武王者”的谶言,太宗听到后,并没有从武姓女子亡天下的思路展开调查,而是shā了宿卫的名将李君羡。
陈尚君说,根据出土的李君羡墓志记载,事发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太宗去世前的一年。
陈尚君估计当时太宗身体不好,对太子李治的能力也不尽信任,某天李君羡宿卫当值,与太宗聊起家常,无意中说到自己的小名是“六niáng子”,由此让太宗想到取女孩名字的武将正合谶言,于是李君羡被shā。
仅凭联想,无端被shā,伴君岂止如伴虎。
但是谶言能shā人,有时也能驭人。
比如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到高宗的皇后,又与高宗并称“二圣”,到高宗身后垂帘听政,最终自立为帝,这个过程中,她最信任的肖小薛怀义之流揣度圣意,wěi zào《大云经疏》,论证女身可以称帝,同时编造众多歌谣童言,以证武氏称帝是上合天命,下协民情。
《大云经疏》中引童谣:“猷水竭,武井溢,此中当有圣人出。
”《推背图》中说:“止戈昌,女主立正起唐唐。
”止戈为武,所指正是武则天。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5期,吴葆勤主编
近几年我一直在各地寻访东坡遗迹,故与东坡有关的文章最喜阅读。
本期中有丁楹的《苏轼心灵解脱模式的来龙去脉》,谈到苏轼一贬黄州,再贬惠州,三贬儋州,受到各种打击,他是如何作出相应的心理调整呢?文中提到了王兆鹏的观点,称苏轼有一套心灵解脱的心理公式,这个公式叫“譬如当初”。
王认为,人的痛苦往往是失落的痛苦,如果你拥有后被剥夺就特别痛苦,但苏轼能够把心态调整到没有拥有之前的状态。
比如苏轼说:“昔我未尝达,今我亦安穷”,“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须吃糙米饭过一生也。
”丁楹认为,这些都“表达了东坡强烈的从逆境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因为人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只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能让心情宁静下来。
丁楹说,“譬如当初”的心理解脱模式并非始于东坡,而是来自于庄子,庄子妻去世后,庄子击缶而歌,惠子质问他,庄子说了一大段超脱的话,以此说明当面对不可改变的事实时,人要从心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陈尚君在《大历十才子发覆》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大历十才子的名单,发现三套名单涉及15人,并认为这是个特定的小圈子,“不足以代表大历诗歌的最高成就”,因为在大历时期,盛唐一流诗人杜甫、岑参、元结等都还在,在京城之外还有很多重要诗人,比如韦应物、刘长卿、皎然、张继等,那为什么有“大历十才子”之说呢?陈尚君分析出这十才子主要是权相元载、王缙的门客,所以陈尚君觉得,十才子毕竟只是有才而地位较低的小官,他们不是门客,“只是才子,只是清客,只是助兴而已”。
杨焄《“不求甚解”别解》专谈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此语被后人用烂,但陶渊明为什么说这句话,后世各有看法。
元人李治的解读是“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清方宗诚进一步解释说:“(陶渊明)嫌汉儒章句训话之多,穿凿附会。
”但是杨焄认为,东汉末年学术风气已发生变化:“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
”既然如此,“陶渊明还有必要予以影射讥评,着实令人生疑。
”对于陶渊明的心态,杨先生在文中谈到他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隐时仕的摇摆,最终以“不求甚解”的心态去当一位“兴趣至上、自娱为主的‘普通读者’,归根到底,恐怕与他最终做出的人生抉择一样,都源于对自身性情、志趣和能力的切实估量和充分践履。
”
《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6期,吴葆勤主编
高峰所撰《李煜的前世与后身》中谈到李煜天生异禀,比如陆游在《南唐书》中称李煜“一目重瞳子”。
高峰说历史上有重瞳异相中的人包括上古传说中的虞舜和秦末西楚王项羽:“由此李煜被认为是虞舜、项羽的后身”。
高峰还谈到李煜与虞舜确实有相同之处:“都娶了姐妹二人为妻,”
虞舜娶了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
李煜则先纳大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妻,此即大周后,其名与唐尧之女一模一样,大周后去世后,李煜又娶其胞妹为妻,此即小周后。
重瞳子项羽与李煜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悲剧性历史人物。
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李煜于开宝八年亡国遭俘。
当年项羽被围时唱出了沉雄悲凉的《垓下歌》,后两句反复咏叹“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李煜在亡国时所填《破阵子》中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论者为此词淒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
”
关于李煜的后身,有人认为是宋徽宗赵佶。
宋人赵溍在《养疴漫笔》中称“徽宗即江南李主”,还有人将纳兰性德与李后主并提,例如周稚圭说:“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
”这样的比较使读者更容易将他们的身世与词风作联系,也更能体会词人当年的心境。
《中国收藏》2021年09期,方晓主编
因为疫情影响,近两年的艺术拍卖使藏家很难到现场看预展,秋季大拍原本大多安排在十一月,今年纷纷推迟到了十二月,很多公司都开始流行在网上看展品,但这种看法类似隔山买牛,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可是从今年流行的NFT拍卖,却让人重新审视实体拍卖,甚至是实体收藏的意义所在。
本期中有记者采访香港亚洲数位艺术展联合总监伍常先生之文,此文的题目是《NFT,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
该文首先解释什么叫NFT,即Nno-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以我的理解,其实就是虚拟艺术品。
今年三月,美国艺术家迈克·温克尔曼创作的数字作品《每一天:前5000天》,以6934.625万美元拍出,瞬间引起市场收藏,为此迅速地出现了NFT交易平台。
为什么NFT艺术如此之火,按照伍常的说法,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线下活动无法进行,迫使交易转到线上,但这也正是推广数字艺术作品的时机。
伍常是如何看待《每一天:前5000天》的高价成交呢?伍常说,购藏这幅作品的藏家维格尼什·桑达雷桑是最高投资以太坊的一拨人,也是全球最重要的NFT基金Metapurse的创始人,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价收购此画的最大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收藏虚拟货币及NFT作品收藏。
从现实结果看,他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加入到NFT 的创作中,比如英国著名当代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物就在网上销售由1万个NFT组成的作品“货币”,每个NFT售价2000美元,藏家可以选择是否将NFT兑换成实体作品,如果选择NFT作品,那么实体作品将被销毁,反之亦然。
文中谈到了NFT是否有未来,以及对于现实画廊的冲击问题,这种新生事物没有时间的考验难以给出准确的本文重点。
伍常也说,NFT艺术在中国内地的发展空间取决于官方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是持续监管还是予以开放。
我对于虚拟之物有着强烈的抗拒心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觉得现实与虚拟之间界限模糊:究竟是活在现实中,还是活在了虚拟之中,我已经搞不清之间的区别了。
《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年第2期,孙宝林主编
本期中谢辉所撰《16—18世纪欧洲对中国印刷术的认识》乃是以西人视角来看待中国印刷术的问题,文中谈到利玛窦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的所言:“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是斫取一块梨木或苹果木板,板面要平滑无节眼。
或取一块枣木板,把一张想刻的字或画反贴在上面,然后极熟练地将白纸挖下来。
”中国人把出版称为“付之梨枣”,可见古书雕板大多是用梨木和枣木为材质,但利玛窦却说有苹果木,不知他是从哪里了解到的信息。
法国杜赫德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持这种说法:“板片用苹果木、梨木或其他坚硬平整的木材制成。
”难道中国人真的用苹果木做过雕板?可惜我没有看到原文,不清楚是不是在翻译时出了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真有人用苹果木刻过雕板。
利玛窦没有详细描述刻板的方式,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将西书与中国书做了比较:“他们印的书不像我们的有两面,只有一面,但他们的书看起来像两面刻印,其原因是,白的一面折叠在内。
”康熙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李明在给朋友的信中则谈到了写样问题:“想印书的人首先请一位出色的书法大师为其抄写。
”古人能雇书法大师来作写样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但李明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觉得“印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是否雇佣了一个好书法家”,想来他说的应当时字体的好坏,因为书法家恐怕不会像手民那样亲自操作刷板。
对于如何刷板,明万历年间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在《日本教会史》中谈到中国雕版印刷术时说:“他们以用水研磨的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墨汁涂在板上。
他们并不像我们添加油,而是使用与一般书写相同的墨汁。
”陆若汉在明万历五年就作为传教士童仆来到日本,时年仅16岁,他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1601年被驱逐到澳门,此后又曾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崇祯年间还因朝廷之请,押运西洋火pào至京,所以他对中日两国情况都较为熟悉。
陆若汉在观察雕版印刷时注意到很多细节,因为谷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术用的是油性墨,以熟亚麻仁油加入碳黑等制成,此墨适用于金属活字的印刷,而中国雕版则是水性墨。
但是格鲁贤在1785年出版的《中国通典》中却进一步点明,中国印刷用的是墨汁,而非墨锭研出的墨:“印刷所用墨汁是一种特殊的pèi fāng,它是液态的,不同于zhī作墨条的pèi fāng。
”
利玛窦注意到了中国人用铜活字印书的问题,他在《天主实义》中说:“又观铜铸之字,本各为一字,而能接续成句,排成一篇文章。
”关于中国金属活字是铸还是刻的问题,至今学界没有达成共识,按照利氏的描述,似乎是铸造。
同时中国金属活字究竟是不是铜制,也有广泛争论,而利氏却在此明确说是铜。
陆若汉在其文中也说是铸造:“每枚字钉均独立制造而成,或用木头,或用金属铸造。
”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中国人强调是北宋毕昇发明的,要比谷登堡更早。
有的西方人承认这一点,比如西班牙埃斯卡兰特在1577年写成的《远航记》中说:“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很多年就使用印刷的书了。
”利玛窦也说:“他们的印刷术要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5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而法国的杜赫德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说:“中国人对欧洲印刷术的方式并非一无所知,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活字印刷术,区别仅在于,我们的字钉用金属制成,而他们仅用木制。
”
《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年第3期,李国奇主编
本期的专稿是印刷字体的演变史。
该期第一篇乃是对朱永新先生的高端访谈,题目是《印刷术催化现代阅读学》。
朱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从印刷术的gé mìng开始的,“没有印刷术的出现,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阅读学的出现。
”因为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人类的沟通基本是靠表yǎn和口语,它是即时性的,印刷术的产生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和传播上的特权,使知识和信息能够以文字的形式大量复制和传播,所以说,印刷术的可复制性是它非常重要的特点,阅读与书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朱先生认为阅读不止是个人行为,一方面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知识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传承文明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来说,阅读极其重要。
国际阅读学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下越来越多的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数字阅读、网络阅读,书和非书的界线开始模糊不清,在电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的冲击下,浅阅读流行,对经典的啃读日渐式微,但朱先生觉得,网络阅读和纸面阅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对于印刷字体的变化,本刊以由近及远的方式予以排列。
孙明远在《中国字体行业的历史、现状、问题点及展望》一文中,讲到1949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文字改革全面启动,确立了从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的方针。
20世纪90年代,在计算机字库市场需求量大增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方正、汉仪、华光等十余家从事字库开发的企业,字库数量迅猛增加,而今各种印刷字体有30余种,加上变形字体共有百余种之多。
刘钊、杨翕丞合撰的《西夏字体研究与Noto西夏宋体再设计》专谈西夏文的数字化。
文中提到西夏国由党项人于1038年建立,西夏努力吸引汉文化,起用汉人官员,命野利仁荣创立西夏文,随着大量文献出土,西夏文研究越发受到重视,而西夏文献数字化具有重要性。
以往对西夏文的数字化,都是通过软件造字,但是有些造字在转化时会变成空方框,在这种背景下,谷歌公司开启了Noto字体家族项目,“Noto”的意思是“No Tofu”,就是无豆腐之意。
因为计算机上的缺字,其字体轮廓通常出现豆腐形方块,谷歌要消灭这种方块。
经过收编和设计,谷歌于2019年发布了新的西夏文电脑体,这对于西夏文的数字化提gòng了很大bian利。
汪文在《楷书,从书法到印刷字体》一文中谈到汉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五个阶段,就目前来看,楷书可以说是汉字发展的终极形态。
他点明了楷书是右手书写的结果:“撇、捺、钩,没有向左上抛的笔画。
撇捺的曲率不同。
说到‘竖弯’,自然想到的是往右弯,而不是往左弯,抑左扬右,上紧下松,这些都是右手书写的必然结果。
”
李开升的《雍正汪亮采本〈唐眉山集〉版本之鉴定》是我最期待的一篇文章。
几年前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在天一阁组织目录版本学研讨会,天一阁拿出不少珍善之本让与会者欣赏,其中就有这部《唐眉山集》。
当时李开升与众人商讨该书究竟是不是活字本的问题,我翻阅之后给出肯定意见,可是再看下去,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这些年来因为收藏活字本之故,渐渐掌握了此类版本的信息,基本上能够做到一望即知,很少会有像面对这部书时的犹犹豫豫,而今阅读李开升的这篇文章,看到他已给出本文重点,为了佐证这个本文重点,他还从书中集出许多字体予以比较,这种认真态度最令我佩服。
《文旅潜江》2021年6月,杨代林、毛向华主编
蒙贺亮先生美意,将我所写《甘鹏云年谱长编读后札记》刊发在本期《文旅潜江》上,故得此样刊。
此刊让我了解到潜江一地有哪些人文遗迹,比如本期中杨金德所撰《桃花源地理原型在石首桃花山》。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究竟写的是哪里,一千余年来,全国有很多地方都在认领,自称他们那里就是桃花源,但杨金德此文另辟蹊径,他说陶渊明这篇短文中出现的唯一真实人物刘子骥当时就居住在石首境内。
杨金德认为,《桃花源记》全文明显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九成篇幅是虚构部分,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全篇的写实部分:“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杨金德说,这一部分看似是全篇一个可有可无的尾巴,但却写到了一个真实人物刘子骥。
接下来他引用《晋史》中的所载刘子骥上山采药的传奇故事,同时说,公元401年前后,陶渊明曾在江陵任江州刺史桓玄手下参军,刘子骥居住的阳歧距江陵200余里,故杨金德认为:“显然,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并将刘子骥写入其中,与他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
接下来杨金德在文章中考证,刘子骥采药是哪一座山。
在他看来,刘子骥只可能在本地采药,而本地大部分山都是低山,在这样的山上采药不可能迷路,他可能迷路的山,只有石首东边45里的桃花山。
《无锡文博论丛》2017年第2辑,刘宝山主编
本期中有龚景春所撰《苏东坡无锡诗歌二题》,文中讲到苏轼两次任职杭州,并到常州、镇江一带赈灾,又一度任职湖州,所以屡次路过无锡,虽然公务冗杂,来云匆匆,但他仍然忙里偷闲游览山水,现存涉及无锡的诗歌有十多首。
龚景春一一考证出东坡所写为何处。
路晓农所撰《梁祝诗词,文苑奇葩》讲到最早的梁祝诗是唐李蠙所作《题善权寺石壁》,李蠙为唐宗室后裔,武宗会昌元年(841)进士。
李蠙未第前曾在善权寺修读五六年,其借榻之处就是元祝英台的读书处碧鲜庵,因为善权寺是李蠙的发迹之地,而该寺在会昌灭佛运动中被毁,后来李蠙上奏懿宗皇帝,要求用自己的俸禄收赎重建,同时将其所赎“碧鲜庵”三个大字刻于石壁。
故路晓农认为,这不仅是南齐《善卷寺记》的重要见证,而且本身也是中国早期的梁祝直接记载。
对于梁祝化蝶的描绘,作者认为最早应当是南宋初期理学家薛季宣来宜兴游览时所写诗句“蝶舞凝山魂”,而词牌名《祝英台近》则始见于《东坡乐府》中的《祝英台近·挂轻帆》。
关于文献整理,本期有蔡卫东先生所撰《无锡博物院藏郑文焯书札册释读》,该文以笺释的方式先将手札原文作标点,而后论述每一通手札背后隐含的故事,再以其他文献予以佐证推论,形成谨严的证据链。
《古籍保护研究》第七辑,饶权、钟英华主编
本书乃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承办的系列出版物,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刊设有固定栏目:古籍保护综述、普查与编目、修复与装潢、保藏与利用、再生与传播、人才培养、史事与人物、版本与鉴赏 、书评与书话以及研究生论坛。
编辑部主任是王振良先生,故每期后有他所写编后记以及征稿启事。
本期中有吴庭宏所撰《古籍修复原则与方法研究》,其副题为“以黄丕烈藏书题跋之古书修补论述为基础”。
作者认为,古代藏书家多重视图书修补工作,黄丕烈为古书装潢代表性人物之一,其提出的古书修补观念对当代古籍修复“整旧如旧”基本原则的确立仍有启发作用。
比如黄丕烈在宋刻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的跋语中提到,他为了修此书耗时逾两年,且修复费用超过书价一倍以上。
吴庭宏认为,虽然修书的具体工作是由工匠操作完成 ,但装修之前的修补方案是黄丕烈自己确定的,“其目的是让工匠在装潢古书时保持古书原貌。
”
又比如黄丕烈在宋本《史载之方》的跋语中说:“余之惜书而不惜钱,其真佞宋耶?诚不失为书魔尔。
”姚伯岳先生很赞赏黄丕烈的修书观念:“今日装修古书的一个重要原则——‘整旧如旧’,早在乾嘉时期就由黄丕烈开始倡导力行了。
”(姚伯岳《黄丕烈评传》)
何义壮撰、凌一鸣译《马泰来先生琐忆》勾起了我的回忆。
大概十余年前我在编《藏书家》时,曾向马泰来先生约稿,之后与他有了多次交往,他为人谦逊,作事谨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马先生在2020年1月于美国去世了。
而今读到此篇文章,方让我对马先生的经历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马先生出生于广州,1949年全家回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他的老师之一是世界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
马泰来在高中时代就对目录学有了兴趣,毕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在那里研究远东图书馆学,后来跟随何炳棣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学习中国历史,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明代私立书院(1368-1644)历史发展:组织和社会影响》,从1987开始,他担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1997年。
1997年底,马泰来搬回香港,在母校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任馆长。
他曾修订林纾所译xìǎo shuō索引,并且发现最早论述《金瓶梅》文学价值的人是谢肇淛,他的文章被《金瓶梅》的法国译者雷威安称为“了不起的文献发现”。
何义壮说,马先生最具影响力的发现是找到了宋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因为此诗是关于《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的,由此说明宋江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同时马先生证明,历史上的宋江的确已经投降。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宋江投降的相关记载是对农业起义的诬蔑与诽谤,但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指出,事实就是事实,马先生的发现是不可否认的。
2001年,马泰来就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当时该馆因藏书量太多,只能买一些金属书架来盛放,但是这些现代化的书架与原馆的古朴木质设施很不协调,既影响美观,还阻碍了室内的空气流通,马先生说服他人,将纪念已故牟复礼教授的基金作为更换书架的经费来源。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马先生身兼图书馆员和学者双重身份,致力于研究明末藏书家徐渤的收藏与活动,他对《红雨楼题记》及《徐氏家藏书目》的辑注,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古籍保护研究》第八辑,饶权、钟英华主编
本辑中郭玉海所撰《甲骨传拓规范刍议》一文专谈当代博物馆如何zhī作甲骨文拓片的问题,文中提到晚清刘鹗在《铁云藏龟序》中谈及编纂此书时,延聘王瑞卿“竭半年之力,精拓千片”,郭玉海算出王瑞卿日均传拓约十片,并指出甲骨传拓速度快慢,是因甲骨大小厚薄以及坚实与否差别巨大,难以一概而论。
经过实践,他们四位传拓人员日均传拓甲骨确实也是十片,看来刘鹗所言并非虚构。
本文谈到,传拓甲骨最好用旧宣纸和旧烟墨,纸墨需要先期存储十年以上,因为新宣纸质脆不堪用,必须多年存储,消去火气。
他同时说甲骨系龟甲兽骨等有机材质,尘埋于地下逾三千年,故在传拓时很容易破碎,因此传拓的基本原则是要保证甲骨安全,比如有明显糟朽粉变者不拓,有原始书写痕迹者不拓,甲骨文内填有朱砂等颜色者谨慎传拓等等原则,同时也一一列明了传拓操作流程。
李致忠先生《连四纸误为开化纸考论》一文,从多个侧面论证了当今市场上艳谈的开化纸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如他认为,开化纸、开花纸、桃花纸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唐虞世南在《北堂书钞》中引用东晋《桓玄伪事》云:“诏命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说明东晋时已有“桃花纸”的名色。
对于开化纸的名色,李先生引用了明倪岳《清溪漫稿》卷二十四所收《保竹公小传》中所载:“券书何纸所写?春曰 :‘开化纸’。
命左右取纸示,曰:‘是也’。
”
而后李先生论证了开化纸不产自开化县的问题,接下来又谈到连四纸广泛用于印书。
他在该文中引用了几十段翁连溪编、广陵书社出版的《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中有关史料,以此说明通常人们所说的殿版开化纸其实是连四纸,接着他指出人们误认连四纸为开化纸,其始作俑者可能是曾国藩。
李先生谈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曾纪刚所写《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中找出了内府档案中所载“开化纸”一名,由此说明,宫内印书确实有开化纸,而当时用开化纸所印乃是乾隆三十年《时宪书》。
丁延峰、丁一所撰《覆写抑或仿写?——以毛氏汲古阁影抄本为例》颠覆了业界对汲古阁影抄本的固有认定。
文中称古代抄书分为一般抄本与影抄本两种,虽然历代对毛氏影抄本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到底毛抄是不是影抄,需要作深入探讨。
按照传统概念,影抄是用透明性纸张覆盖在原书上,然后用笔依原字完全摹写。
但是,这种作法在摹写时容易透过纸张污染原书,宋元本很珍稀,应该少有人舍得如此摧残,更何况作者发现今天各家图书馆所藏的毛抄本实际都是仿写本,并非覆写。
作者为此给出了三条理由:一是这些毛抄所用纸张皆为白纸,较厚,并不透明,根本看不到底本之字;二是影抄本与原本对比字迹不同;三是毛氏影抄本是多有异体字甚至误字,并作过涂改,如果是覆在原本上影抄的话,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第四宋刻本原装皆为蝴蝶装或包背装,但现在的毛氏影宋本皆为线装,从装池上看显然已非原装;第五,两者间的刻工、版框尺寸等都有差异。
所以作者认为,古人所说的影抄,其实是一种仿写。
《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0期,黄乔生主编
本期主题是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
其中刊发有《日本学者笔谈一组》,首先是下出铁男作、王俊文译的《“人之子”阿Q》,该文谈到阿Q被拉往刑场,众人围观喝彩,xìǎo shuō的这一结尾令其不寒而栗,使之想起了《复仇(其二)》篇末描写耶稣被钉shā在十字jiá上的一节。
作者认为,耶稣是“人之子”,同样阿Q也只能是“人之子”,他觉得鲁迅让阿Q背负了太多的东西,并且认为:“光嘲笑蔑视阿Q的愚行,并不能体会他所受的苦难。
”下出铁男想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那一句:“宗教是人民的yā片”。
但是下出铁男更收藏这句名言前面的部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宗教里的悲惨既是现实的悲惨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悲惨的抗议。
宗教是被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
”下出铁男说,这些话反映了马克思对于宗教的卓见,他觉得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宗教。
伊藤德也的《连载xìǎo shuō〈阿Q正传〉的幽默》中,谈及该xìǎo shuō从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1月12日 《晨报副镌》上连载,他认为鲁迅这么有规律的在刊物上连续发表的,就只有这一篇《阿Q正传》而已。
鲁迅后来写到:“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
”鲁迅说:“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
”伊藤德也夸赞孙伏园善于催稿,“如果孙伏园不催鲁迅每周写一定分量的文章,《阿Q正传》就根本不能成立的。
”他说鲁迅写了几十部作品,《阿Q正传》可算其代表作。
他将《阿Q正传》的篇幅与《孤独者》《伤逝》等做比较,发现只有《阿Q正传》的一半左右,鲁迅说过“我没有才能做长篇作品”,伊藤德也说鲁迅的确擅长短篇作品:“但是鲁迅他没有的不是‘才能’,而是机会或者环境、条件。
”
桥本悟在《“阿Q”,科学与文学》中,注意到鲁迅曾经说过的:“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桥本悟说,鲁迅这句调侃之语尤其讽刺了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因为胡适自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同时桥本悟认为这句话也暗指胡适所倡导和引领的整个历史科学的新方法,他认为“科学的态度以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这进而暗示了进步的时间观,即随着 时间的推移,关于世界的知识会不断扩张和积累。
‘速朽’的时间观则从内部瓦解了进步的时间观。
”
秋吉收的《关于台湾的“两种”〈阿Q正传〉》中,谈到台湾最早把《阿Q正传》翻译成日语的是杨逵,该文的介绍能够使读者了解到宝岛台湾对于《阿Q正传》的连载等问题。
标签: 骓的繁体字怎么写(「书物」2021年12月师友赠书录(九)韦力撰)

